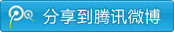众里寻他千百度!发展模式何处寻?多少年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模式上,我们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正如“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只有冥思苦想才能得到完美答案。IDM? Foundry? Fabless? 虚拟IDM?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
抛开企业个体发展来谈产业模式,或许您会觉得是论“水中月,镜中花”,诚然每个企业的良好发展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基础,是“如何做”的实践论的执行者,但作为探索“以何做”的方法论,尤其是思考产业整体发展的顶层设计来讲,模式的确立是“谋定而后动”的前提。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半导体发展到底该采用什么模式。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解开中国半导体发展模式的“斯芬克斯之谜”。当然由于我才疏学浅,以及几千字的篇幅肯定很难全面、系统、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而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以及我的深思浅见,以求“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业界探寻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只好“窥斑见豹”,在探索答案之前,先简要看一下半导体产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寻找发展模式之前的产业突破点。首先从韩国说起,韩国因为国家小,民族性等“国家加市场”的多个“小而精”的特点,采取的是“点式”突破,比如重点支持个别企业(比如三星),先寻找某一个突破点(存储器),来作为发展半导体产业的突破点;而台湾则因为岛屿原因,没有产业纵深(当然,目前大陆就是台湾的产业纵深。但在台湾半导体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基本没有利用大陆的纵深),选择了做专做精、分割产业的“线式”突破,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环节,比如在Foundry和封装这两条线上寻求突破,通过深耕细耘,做到全球第一。进而找到了适合台湾发展的半导体产业模式;而美国则因为强大的产品定义能力、标准制订能力和产品设计与制造能力,采取了从标准、产品定义到设计、制造一体的“面式”突破,这种集大成的“面式”突破为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第一大国,寻找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上述只是对这三个地区一个产业突破点的粗略分析,这个“点”“线”“面”不是上述三地的发展模式,甚至在突破点上也未必能完整来概括。同时日本这个曾经强大的半导体大国的兴衰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而因我对日本产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忽略了这一块。这些都有待业界去深入分析和思考。)
找到了突破点,才能更好地寻找产业发展模式。而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既有着适合自己“国情”或者“地区情况”的个性,又有着国家(“政府”)战略和大企业战略的高度统一以及产业发展上的战略性和市场性的有机融合的共性。在这个大前提下,虽然发展模式不同,但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基础、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才能够殊途同归,成为全球集成电路角力场的佼佼者。
每一种模式或者产业突破点都要符合国情,尤其是能够发挥自己的强项。那我们的强项呢?那就是市场、终端、资本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不想用繁琐的文字来表明中国的市场有多大,我不想用枯燥的数据来说明中国有多少世界第一的制造产品线;我不想用花哨的大道理来阐述终端和芯片结合的重要性。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业界有识之士都想到,也都提到要想发展好芯片产业,必须把中国的市场和芯片结合起来,把终端企业和芯片产业结合起来,把市场和终端的巨大源泉引到芯片产业来。芯片产业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应该是来自市场的需求,来自市场/终端的“水”。“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就是市场和中国的制造与终端企业。或许我们的发展模式还在迷雾中,但在突破点的思考上我想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则可能是集资本、半导体制造、芯片设计和终端制造为一体的“体式”突破点。
但现在我们的系统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和芯片制造之间要么是“老死不相往来”,要么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很难有患难与共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制定标准、定义产品、探讨商业模式的深度合作。如何改变这一切?那就必须要“先恋爱”“再结婚”。怎样引导终端企业和芯片产业的“恋爱”,在市场经济时代,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靠爱国口号也是不行的。所靠的就是“利益”。因为企业都是逐利的。并且也只有有“利益”的合作才能够持续,也只有双方受益的模式才能更健康,更持久。通过投资合作这条链,把大家串在一起。是的,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上或者某一个领域内会因为“相互帮扶”走得慢,但要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要想走得远,就抱团一起走。半导体产业不是百米跑,而是马拉松。我们已经输在了前段,决不能输在后程。
怎样引发终端企业对芯片产业的投资积极性,怎样串联,就是靠投资,甚至相互投资、“隔代”投资(比如Foundry厂如获得设计公司的投资,则对Foundry厂的中立性有损害,但如果设计公司的客户来投资,则这种“隔代亲”的投资不仅避免了上述情况,还为Foundry带来了客户以及对最终市场的理解。“隔代亲,代代亲”。产业投资亦是如此。)。靠这种关系,资本这个无形的手才能把半导体的供应端和需求端结合起来。这里就有我这“十问中国半导体”的核心思考:“堵”“疏”理论。何为“堵”?就是对一定规模的、消耗芯片较多的终端企业(也包括中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国家电网等工业巨头),尤其大企业,比如在申请高新企业、人才政策、税费优惠、研发中心等需要政府“支持”时,对投资芯片产业要有一定的对应要求:那就是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对芯片产业的投资。这个“堵”也就是你在向政府需求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付出。
而犹如治水,治理“终端”这股洪水流向芯片行业这个急需灌溉的良田,必须有“堵”,但更要有“疏”。只有终端企业通过投资赚到了钱,才有积极性。与“堵”相比,这个“疏”更重要。如何“疏”?我有两个建议。一是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政府成立大规模的投资基金,这个大规模投资基金的目的除了进行针对芯片产业的定向投资外,更重要的是配套终端企业对芯片产业的投资。如果一家终端企业投资了芯片企业10亿人民币,那么政府的引导基金可以按照1:1配套10亿人民(比例可以根据产业的发展情况、终端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及需要投资的芯片公司的市场性与战略性进行动态调整。比如投资芯片设计行业的配套比例可以低于投资制造企业的比例。而这个投资必须是对制造、设计、关键设备和材料产业的并存投资。为何半导体的制造与设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在后面的问题“制造与设计的关系”一文中会进行详细地阐述)。而中央可以把中央出资的10亿元人民币中的20%划拨给终端企业的投资。并且中央投资的10亿的分红完全给与终端企业。相当于终端企业投资了10亿元,但享有20亿元投资的分红比例,以及相当于12亿元的股权受益。而同时为了降低半导体企业的政府色彩,提升龙头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基金和被投企业的决策效率,这个基金需要寻求更多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政府基金发挥引导和鼓励的作用,而真正主导的应该是市场化的、具有中立色彩的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国资则作为长期“相对小”股东,发挥种子、引导和杠杆的作用,以“扶持产业为主旨、引导投资为目的”的原则,最终寻找合适的时机在保证“国资不流失”的原则下退出。为了更好地疏通,另一个建议就是尝试在资本市场做文章,对芯片行业的上市企业实施单独排队上市,并购重组单独审核。按照对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对产业等多方面负责的态度来审核芯片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运作。真正起到鼓励芯片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来实现企业做大做强的作用。
有了上面的“堵”和“疏”,这就促进了产业链供需两端的“恋爱”,谈起了“恋爱”,至少改变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思君不见君”的局面。为以后供需两端的“结婚”奠定了坚定的“感情”基础。而在对以后终端公司采纳芯片,或者芯片设计在国内制造的时候,同样可以采用上述的“堵”“疏”理论。最终使得中国半导体产业按照制造、设计和应用的三位一体的“体式”发展突破点,实现了供需两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合作。而在这个思考中,产业链上的企业既有各自发展(利用分工细化的专业化带来的契机)、又有上下合作(解决了中国芯片产业上下游缺乏紧密合作的弊端)的求“统”(结果求“统”)存“异”(发展为“异”)的“体”式突破点后,或许就可以去探寻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模式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了。
俯卷回思,发现在探寻产业发展模式面前的渺小,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找到寻求发展模式之前的产业突破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中国半导体,但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半导体。而对于我们的发展模式来说,依然如此。其实回到“斯芬克斯之谜”,我们都知道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人”。而其实我们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模式的“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何尝不也是人呢。不是我们自己呢!德尔菲神庙前石碑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对我们个人而言,认识我们自己非常关键,而对我们的产业更是如此。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我今天第一问的答案。
后记:虽然近两年来,我和多位WTO专家以及商务部相关领导进行过多次请教,但因为WTO方面知识的浅薄,或许在我的思考中有违背WTO规则的地方。半导体产业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而中国又加入WTO。解决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术”和“战略”一定要符合WTO的相关规则。所以上面的浅见中,外资终端公司也可以参与到对国内芯片产业的投资中来。而在符合某些条件下,对外资芯片公司中国也可以考虑实施进行“选定式”的投资。